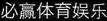近日,读完西南财经大学王擎教授所著《中国经济杠杆研究——高杠杆成因、溢出效应与防范化解》一书,有一种似是故人来的亲切感。毕竟十年前,我们团队给《中国国家资产负债2015》所定的主题即为“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回应并剖析了当年中央提出“去杠杆”的重大决策;后续我们团队还编制、发布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并延续至今。回望来路,中国的经济杠杆调整已走过十年,经历了曾经的“被动去杠杆”到“主动稳杠杆”以及“总量控制”到“结构优化”的深刻转型,不仅在政策实践上进行稳增长与防风险动态平衡的有益探索,还带来理论认知上的提升,引发对杠杆背后发展哲学的思考。
中国近三十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以绝对水平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年以前的平稳发展期,宏观杠杆率从1995年的93.8%上升到2007年末的144.9%,社会债务水平相对较低;第二阶段为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6年为杠杆攀升时期,全社会债务水平(尤其是房地产相关部门)上升较快,宏观杠杆率在9年内上升至238.6%;第三阶段为2016年至2019年的强力去杠杆时期,宏观杠杆率增速放缓,至2019年末为246.6%;第四阶段为新冠疫情后的5年,在支持性、扩张性政策措施影响下,杠杆率继续缓慢波动攀升,至2025年一季度维持在298%左右。
总体上,中国宏观杠杆率风险呈现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中国经济杠杆的周期性修正不明显,即在经济上行期杠杆率增加,在经济下行期却不降反升。二是杠杆率结构相较其他经济体存在异质性。中国杠杆率风险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而发达经济体风险则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与居民部门。
站在2016年前后的节点,中国经济处于重要战略转型期和机遇期,高杠杆问题以及相关的“黑天鹅”“灰犀牛”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非常突出。彼时,正如《中国经济杠杆研究》所言,政策界、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对中国经济杠杆的分析不能仅限于对绝对数值的关切,而应深入到其背后的生成逻辑,尤其要从中国的体制机制特征入手。
第一,经济杠杆折射的是中国经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在我国实体经济总债务中,企业债务占六成,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债务占六到七成,国有企业债务中,近一半为融资平台债务。我曾用过“四位一体”的体制特色来归因国有非金融部门高杠杆现象——即国有企业的结构性优势、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与软预算约束、金融机构的体制性偏好以及政府的隐形兜底责任。国有非金融企业在债务形成过程中存在政府隐性担保的支持,加上地方政府和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进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置产生诱导,使得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杠杆率产生结构性分化,推动国有企业部门继续堆高债务融资,这个逻辑闭环是导致我国经济高杠杆的最重要机制。
第二,危机应对措施潜在地加速了杠杆的结构性错配。危机冲击往往致杠杆率迅速攀升,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0年IT泡沫破灭,均导致了我国杠杆率的阶段性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进入快速加杠杆阶段。当年大规模刺激措施出台“快准狠”,成功避免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与此同时,也因为这些扩张性政策,导致出现了一系列“后遗症”,其所积累的风险有些直到今天还处在“消化”阶段。杠杆率的结构性错配(如高效企业可能配置低杠杆,而低效企业却配置高杠杆)加剧即是“后果”之一。大规模的信贷刺激计划延迟了经济体中劣后资产的出清时点,推高了“僵尸信贷”和企业负债,导致企业杠杆大幅上升,降低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是随后中央“去杠杆”政策出台的重要触发因素。
第三,房地产过热导致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我国家庭部门总体上是净储蓄的提供者,杠杆率显著低于企业部门。但相比于欧美国家家庭杠杆在2008年危机后的下降趋势,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一直处于较快上升阶段。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统计,过去15年来,宏观经济各部门中,家庭部门杠杆率的提升幅度最大,从2008年的17.9%提升至2025年一季度的61.5%,增加超过了2.4倍。而家庭部门债务的最大组成部分为房贷,也即家庭加杠杆的主要对象是房产,这是过去几轮经济增长周期中的基本模式。此外,家庭部门的杠杆率风险也有结构异质性,其中投机性房地产投资,非首套房家庭的购房行为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四,要高度警惕杠杆上升过程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周期突显了信贷周期以及房地产周期的共同作用。本质上,金融资产负债表和实体杠杆互为“镜像”,信用扩张过程中,资金从金融流向实体部门,再回流至金融部门,金融机构的扩表与实体部门的加杠杆是信用派生的两个面。同时,金融部门也是政府施加调控政策和直接刺激经济的重要抓手。银企借贷行为中的软约束和僵尸信贷,不仅导致非金融企业的结构性加杠杆,也助推了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部门的资产规模和结构变化,并加重金融系统性风险。正如我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系统性风险呈上升趋势,其中金融部门的系统重要性最高,而清理僵尸企业能优化宏观金融网络结构,降低系统性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均强调要持续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
第五,优化增长范式是实现经济“好杠杆”的根本途径。中国经济金融结构中客观存在杠杆率上升的内驱力,要根除之,必须改变传统的信贷驱动增长模式。回顾过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几轮信贷扩张、债务攀升、杠杆率上行的初衷都是以宏观政策支持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转型;检视当下,中国经济高杠杆现象可以视作传统增长模式疲态初露与转型挑战已现端倪二者叠加的阶段性产物。因此,杠杆本身并不是政策目标,因为其本质是中性的,其作用取决于“使用效率”和“结构分布”。政策出发点应该落在如何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壮大内需驱动力,促进经济转型。
基于上述认知,近10年来,中国在降低宏观杠杆率增速、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调整过程既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目标,也有效应对了贸易摩擦、疫情冲击等复杂经济冲击。
一是政府部门隐性债务压力缓解,杠杆率可控。一方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的势头基本得到控制,使用“开前门、堵后门”方式积极稳妥化解债务,各类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相关的传统金融工具规模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加强财政纪律,地方政府债务“预算软约束”开始向“预算硬约束”转变,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总体来说,目前显性政府债务仍有较大空间,地方隐性债务增速显著放缓。
二是企业部门杠杆率趋稳,结构优化。通过“债转股”、混改等市场化方式,国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实现快速压降,大批“僵尸企业”得到积极处置。同时,多部门政策协调,打破管理部门、企业自身、金融机构、社会信用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硬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此外,政策层也在努力推动杠杆结构优化,如出台普惠金融政策(如定向降准、再贷款)推动民企贷款增速回升,信用债市场分层机制逐步完善,高杠杆民企风险有序出清。2016年之后,企业部门杠杆持续多年增速较低,至2024年,8年中只增长了10个百分点左右,有效遏制了“隐性担保—预算软约束—企业部门高杠杆”这一动态机制的作用。
三是房地产相关债务风险下降。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随之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有效遏制了20年来房价加速上涨的趋势,也抑制了家庭部门通过房地产加杠杆的冲动,家庭“过度负债”问题有所缓解。中国经济正逐渐摆脱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四是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我国金融杠杆率明显下降(资产方统计的金融杠杆率从2016年高点的77.9%回落至2024年末的51.2%),金融资产脱实向虚、盲目扩张势头得到扭转,银行业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有效推进,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得到稳妥处置。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当前的宏观杠杆调控更注重“提质增效”,旨在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支撑消费增长,bwin官网最终实现控债务与稳增长的良性动态平衡。
总体而言,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通过结构性调控、市场化手段、统筹协调和制度完善,中国在降低宏观杠杆方面实现了总量趋稳、结构优化、风险可控的阶段性目标。现今的政策逻辑已从“去杠杆”升级为“优化杠杆结构、提升杠杆质量”,让债务服务于创新驱动、消费升级和高质量供给。
回首经济政策与宏观杠杆之间的微妙平衡,从“总量控制”到“结构优化”、从“风险规避”到“质效提升”、从“短期调控”到“跨期调节”,一方面是政策实践的持续优化,另一方面是认知层面的不断跃迁;而这些,均在《中国经济杠杆研究》一书得到充分体现。
该书主体内容基于2016年中国经济高杠杆风险的态势,通过多种模型,重点分析了我国企业杠杆和家庭杠杆的基本特征、内在形成机理以及其对经济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影响。作者对政府软约束、信贷行为和企业部门债务动态三者关系的刻画最为自洽和深刻,有效解释了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的周期刚性之谜。基于西南财经大学的家庭调查数据优势,作者对家庭部门房地产投资的微观行为分析也非常中肯,较好拟合了2008年之后中国家庭杠杆率的曲线动态。作者的研究有很好的前瞻性,如对创新驱动需要“最优存量债务”支撑的阐释,以及家庭消费降级问题的实证分析,均直指当前科技创新和内需提振,是当下新经济转型的重要关切点;有关金融系统性风险分析,对于推动形成并逐步完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框架具有重要价值。书中的很多政策建议,现在看来都已经落地生效。
值得指出的是,该书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中国经济杠杆的分析和治理框架,这是对传统的债务驱动增长模式的深刻反思,也是探索杠杆背后发展哲学的有益尝试,对于如何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启示。